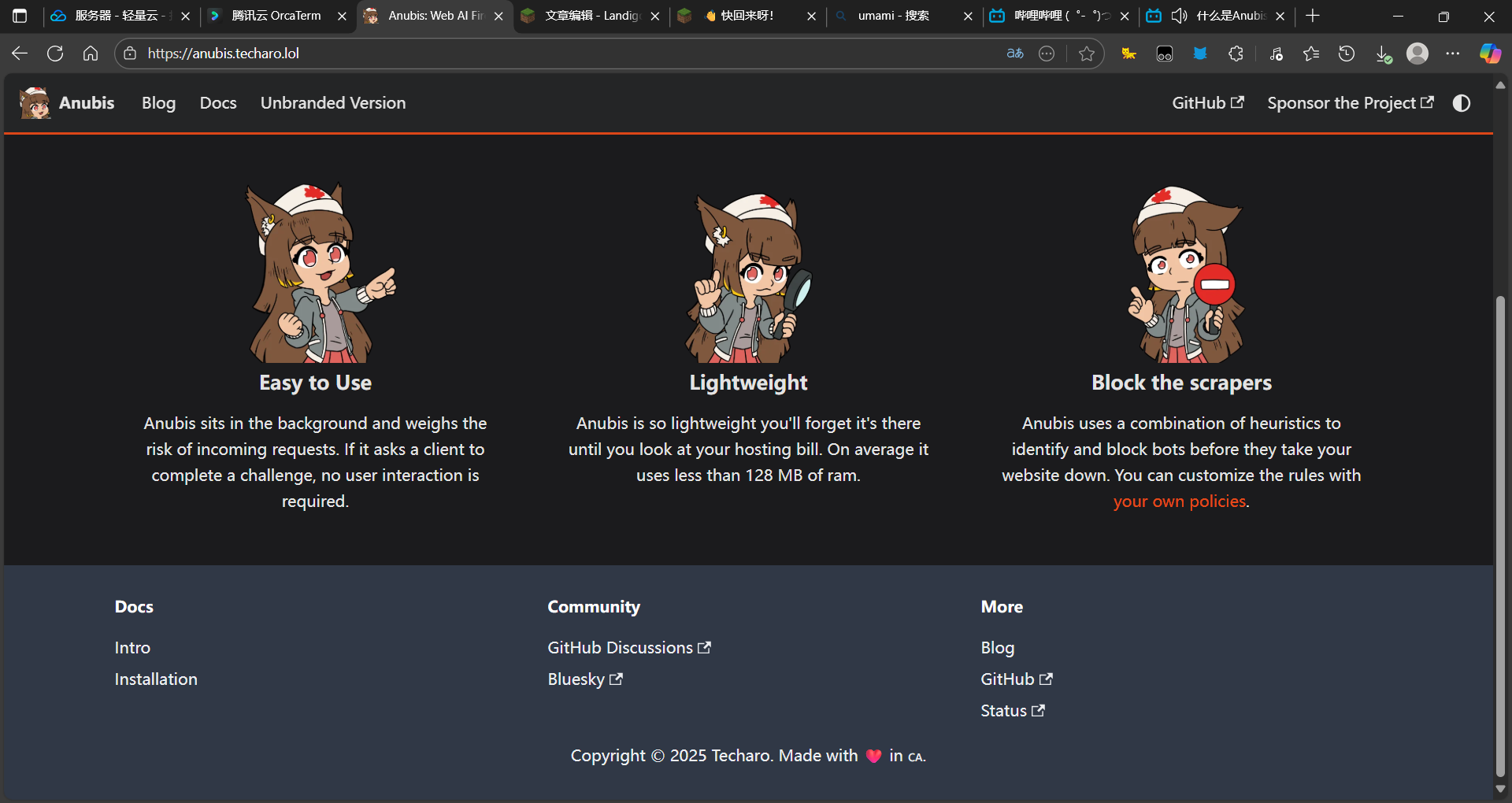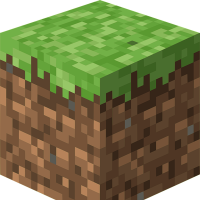作者:微信公众号:逍遥不纪年
人之患,在好为人师——孟子
前阵子和一位年轻老师在朋友圈交锋。他转发了一则明显错误的历史信息,并以此来煽动情绪——这类情况已经很久了。我本想克制,像往常一样翻过就好。但最终,还是没忍住指出来。对方的回应有点尴尬:“当玩笑看的。”我又较真了一句,他回道:“所以我从来不好为人师。”随后又发了个朋友圈表示:“你杠就是你对”。言外之意,懒得理你这个没完没了的老登。是的,老登。前天看二手玫瑰现场,梁姨都变梁姥了,他自嘲,我还配不上叫“老登”,顶多是个“中登”。还真别说,就他那与时俱进的精气神,腻到极致反而清新脱俗。一个人之所以显得“油腻”,并不在于年龄,而在于姿态——自以为是、停滞不前,总想拿过去的经验教导早已变化的世界。这一面镜子,照亮了我自己。
01.
我不自觉地让学生看到一个强势的老师。课堂是我的舞台,我控制节奏、主导表达、牢牢吸引学生的注意。逻辑严密、语言流畅,这些特质确实让我一度引以为傲。但所谓“个人魅力”,其实是一把双刃剑。它让学生沉浸于我的思维节奏,却削弱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;它为我带来讲台上的高光,却也无形中阻断了学生自主探索的可能。我逐渐明白:教育不需要始终站在中央的耀眼角色。真正的教师,应当退后一步,成为那个托举学生的人——用引导代替灌输,用发问代替断言,用倾听代替宣讲。我们存在的终极意义,不是被学生喜欢就可以了,而是帮助他们发现自己,自己成为舞台的主人。而这样的问题,不仅限于课堂。在与年轻教师交流时,我也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“我知道该怎么做”的权威感。缺乏耐心、急于给方案、习惯性地说“你照我做就行”……我以为那是在传递经验,实际上,却是在用我的声音覆盖他们的声音。许多年轻老师还没来得及思考,就已经被我的“连环输出”压得只能点头。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那一刻,我仿佛成了自己曾经最反感的那种人——用经验绑架他人,用资历代替对话。当小徒弟战战兢兢地问:“师父,这个内容,你说的我没听明白……”“师父,这一课,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案例……”小心翼翼的样子,让我意识到,指导的真正意义,不在于复制另一个自己,而在于唤醒对方的潜能。每一个年轻教师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,他们需要的不是被灌输,而是被相信、被支持、被点亮。
02.
过去几年,我走过不同的学校,与来自各地的老师交流。最近几年,因为工作原因我走访了许多不同的学校,也与全国各地的教师深入交流。最初我总带着“培训”的使命感出发,以为我是去“传授”什么。但一次又一次,真正被教育的是我。我曾自以为是地讲授“如何应对学生早恋”,直到一位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初中班主任问我:“老师,我们这儿很多学生不是早恋,是早婚。家长支持、习俗认可,有的孩子已经订了婚甚至同居。我该怎么劝他们回到课堂?”我一时语塞。我所掌握的那些话术,在具体的生活现实与文化语境中,突然显得如此苍白。我讲“家校合作”,语气坚定地说“一定要把家长动员起来”。一位乡村老师轻声说:“我班上百分之九十都是留守儿童,父母一年最多回来一次。打电话都经常断线,您说的‘合作’,我该找谁合作?”那一刻我才意识到,我所说的“家”,和他们所面对的“家”,并不是同一个世界。我谈起班级管理,说到守时的重要性、学习习惯的养成。一位贫困县的班主任站起来说:“我每天教室里总有一半人迟到早退。孩子们下午三四点就要去帮家里运货、摆摊、带弟妹。对他们来说,在教室多坐一分钟,家里就少挣一点活命钱。我不是不想管,我是没办法。”这些声音,一次次把我从理论的空中楼阁拉回地面。我带着一套看似成熟的教育模式走出去,却在每一个真实的困境面前,拥有了敬畏之心。生态之复杂,倒逼我去重新理解教育。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你“教会”了谁,而是在交流的过程中,你自己被一次次挑战、一次次修正。“教师”这个词,总带着几分让人不舒服的意味。它仿佛自带一种姿态:我要去教你。可多年走下来,我越来越觉得,教育是无穷尽的,它从来不是我们掌握了多少答案,而是它让我们一次次面对自己,以为懂的,其实并未真正懂;以为成熟的,其实依然粗粝。
03.
为人师者,最难的大概是管住自己“教”的冲动。经验是好事,也是坏事——它让你自信,也让你容易膨胀。过去,我总觉得“我与我纠缠久,宁作我”这句话,是坚持自我的孤勇。而现在,我才意识到,这份纠缠,恰恰源于没有真正走出去:去拓宽视野,去倾听他人。去打破固守的、已经确信的东西,去走出舒适区,保持吸收、更新与热爱。这种我与他者的关系,放在教育场景里,最高境界或许不是“宁作我”,而是“忘了我”——学习者不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偶像,他们需要一个真实的对照样本,去成全自身的成长。教育终究不是塑造,而是成全。教师的价值,不在于被记住,而在于让学生——忘记你,却成为自己。
教师节快乐